一言难尽的2022我记住了这一秒
· 2023-02-26 14: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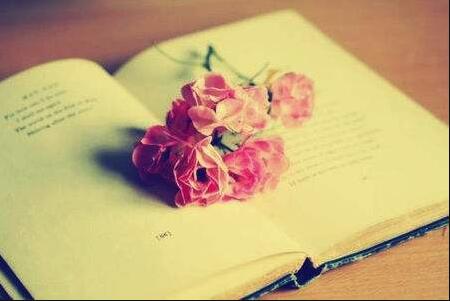
享受生活的英文句子12月31日下午,在小米和徕卡举办的“3万秒长城影展|2022中国影像辞典跨年直播”中,我们看到,3万张记录生活瞬间的照片,在长达8小时的直播中,一秒一张地铺展开来。
在寄托着中国人朴素的民族情感的长城上,3万个瞬间为我们重现了2022,我们看到这一年人们的心灵影像——得与失,光与爱,相聚与告别......人们像水泥底长出的不可战胜的草木,努力生活,构建希望。
拍摄者翁凯仕今年42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公司做着一份普通的行政工作。父母住在距离他60公里的地方,想去探望的时候,开车1小时左右便到。菜市场很近,下楼走几步就到,有空的时候,就买上两三天的量,照着手机里收藏的视频煮一家人的饭。
疫情期间的某一天,朋友带他们全家出去玩,帮一家人拍照。看到照片时候,他有些心动,如果他也能拍出这样的照片就好了。
他为此专门买了部手机来拍摄,手机轻巧,可以随时拍。这成为他记录生活的起点,但那时他还不晓得,摄影为他带来的远不止于此。
他拍了非常多儿子吃饭的镜头,过去没觉得有趣的地方,都变得有趣。他拍母亲抱着儿子在阳台,指着下面马路上的车子讲解,也拍父亲陪儿子玩游戏、荡秋千。
这些互动,是他过去从没关注到的事情。有一次,妻子包饺子,光线照到面粉上,他第一次发现,妻子的手很美。
今年,他系统地学习了摄影,因为其他地方去不了,他将自己周围的地方走了一大半,十几公里之外的海边,走路就能到的韩江,附近学校里的大操场。
每个周末早晨七点,家人还在睡觉时,他便出门去附近的城中村、老房子区和巷子里晃悠,和那里的人聊天,给他们拍照。有时,会走得远一些,去农田里和农民聊天,他能感受到这些人背后的努力。
如今,他走在路上,对街边坚持出摊的小贩、在高楼上进行空中作业的建筑工人以及马路边的环卫工人都有一份敬意。
这张照片里的人,是母亲小区里的邻居,住在楼下一间二十平米的铺位里,因为不临街,这里无法做生意,只是价格便宜,一家子人的起居便都定在了小铺里。
翁凯仕过去也没怎么关注过他,只是有时周末他去探望父母时,会看到他推着水果车出门。母亲说,他十几年来都是如此,供养一大家子人。
今年有一天,差不多四五点钟,他站在七楼看到邻居推着一车水果,投下瘦弱的影子,他带着一丝敬意,用手中的小米手机拍下了他。
父亲已经失去了做手术的机会,只能保守治疗。第一次住院,住了二十六七天,那是父亲一生中进医院最长的一次,而这只是个开始。治疗的效果反反复复,阿漠的心态也在快崩溃与崩溃间往返。
在厦门,阿漠从事着一份装修材料的物流调度工作,朝八晚六,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处理着几乎所有的日常工作和突发情况。
这张照片拍摄于厦门植物园的热带雨林区,七月的某个下午,阳光和雨林区的水汽形成了丁达尔效应,一个孩子被这样奇妙的场景吸引,奔跑进茂盛的植物当中,也跑进了阿漠的镜头中。
这种场景是疫情3年来阿漠头一回遇到,当时他只觉得光线漂亮,父亲生病后,当他再翻看时,才发现,照片里有一种打破黑暗的意图。
今年,34岁的安冉,第一次被迫体会了自由职业。他所在的公司是一家留学教育机构,一直安扎在租金昂贵的国贸CBD中,3年间见证了楼内其他公司陆陆续续地搬离,终于在今年年初撑不下去了,搬去了较为偏远的地方。
安冉的通勤路程一下就扩出了好几倍,他只好转为公司的编外人员,没有底薪,只按课时拿薪水,课程有多有少,收入自然不稳定。摄影是他的副业,然而因为疫情,他在五月份和六月份接的两个异地项目都黄了,一个在云南,一个在新疆,都是他向往的地方。有阵子连北京的胡同都拍不了,他不免感到焦虑,时间多出了很多,创作却减少了。
那天,安冉已经在附近晃悠了一个下午,寻找拍摄的素材,晚上8点,当他准备离开时,突然看到了这间在一片漆黑中亮着灯的办公室。
办公室处于一座老旧的写字楼二层,从一张大窗户望去,安冉几乎能看到办公室的全貌,灯光下,仅有一个人在加班,白色衬衣加马甲,典型的白领穿着。
这是安冉熟悉的,大学还未毕业的时候,他去一家设计公司实习,头一天就加班到凌晨四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加班就成了家常便饭,凭的,仅仅是一点不想躺着的执念。
而今年的奋斗者们,无疑比以往更为艰难,许多人的生活已经全凭强撑。照片里的场景未免过于应景,安冉特意没拍清他的脸,他觉得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在冯杰的印象中,新人拍婚纱照要么在风景壮阔的地方,海边、山脚、丛林等等,要么在浪漫的摆设中。
而这对新人,却是在山城重庆的一个小巷子里,那是一个有些杂乱的环境,人很多,大部分人都在匆忙的工作中。
重庆的夏天很热,连常年在室外工作的大爷都有些面目焦灼,但他们的脸庞在拍摄过程中一直保有笑容。
在海边的一个小楼里,女生在楼梯上写生,天空的云彩像一副浓郁的油画,楼梯下,是一位环卫工人在清洁楼道。巧合出现在一个场景中的两人,却仿佛是生活在2022年的人们的群像。
如果说,2022年,有什么东西变得更好了,那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定是我们和亲人的连接更紧密了。
他是一个即便刮风下雨,都要跑去食堂吃饭的人。在这里,他能看到形形色色的同学,有特别着急的,有两三个人占好椅子等舍友的,也有人吃两口,就要看看手机或文件的。
疫情之下,火车站一楼的候车厅里,孤零零地仅有一名旅客。一束光从穹顶漏下,慢慢地移动,摄影师在二楼候车大厅扶梯口的栏杆边,等待一个多小时,直到光洒在这位旅客的身上,按下快门。
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能在长江滩边遇到躲在阴凉处打盹儿的人,手里还拽着包,看样子休息过后,就要继续去哪。
在一所小学,邱岳担任着信息技术科目老师,听起来并不十分有趣,但作为摄影师的邱岳能将所有普通的事物,都变得奇妙起来。
他用一双敏锐而充满童真的眼睛捕捉到了魔法的世界,在倒数第21秒,我们看到了神奇的《水龙术》。
它拍摄于一天下午3点多,邱岳在学校里宽敞的绿化带,看到正在浇水的绿化工。那天太阳的角度非常妙,邱岳恰好站在他和水中间,从水管浇出来的水在太阳的映射下好像一块水幕,他的影子又恰到好处地映到了水幕上,一个硕大的身影就地而起。
擅长记录的人们并不着力于追寻那些波澜壮阔的场景,而是从我们身处其中的日常中去挖掘碎片,进行重组。
今年7月,小米和徕卡举办了“小米徕卡影像大赛”,129天征集到27万张记录中国人生活瞬间的照片,完成了一份《2022中国影像辞典》。
正是从这27万张照片中选出的3万张照片,组成了在“3万秒长城影展|2022中国影像辞典跨年直播”的3万个瞬间。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是一个属于个人或群体的故事,它们共同汇入了时代的洋流生活记录。
在壮阔的长城上,这些细碎却温润的光影带我们走过了这特别的2022,留下该留下的,继续往前走。
文章推荐: